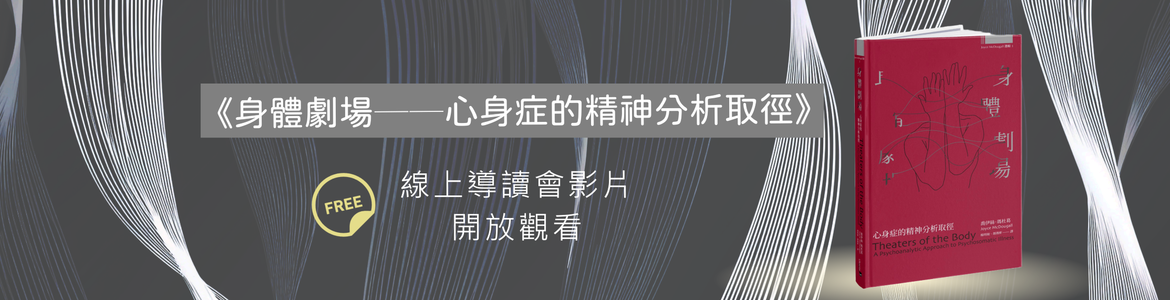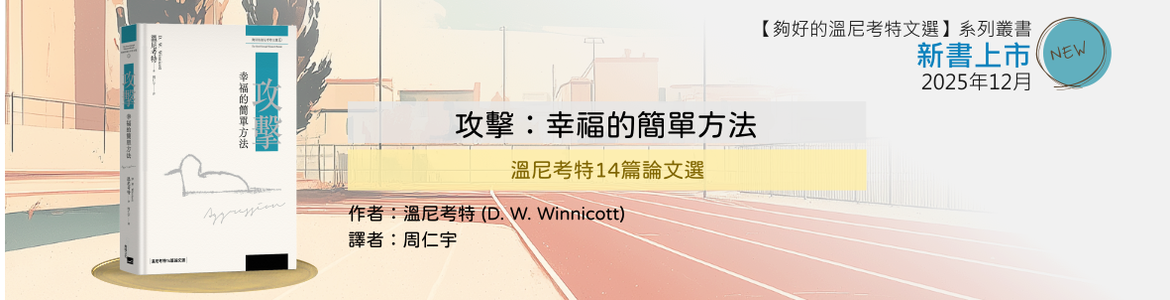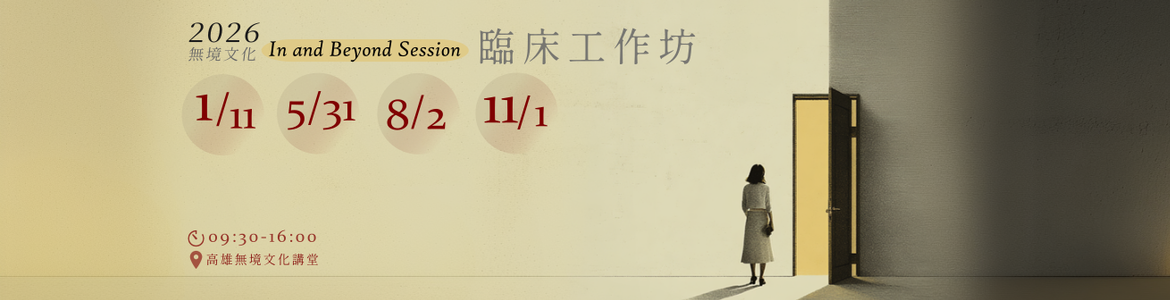【周沛蒨】艾美懷絲的醉鄉靈魂樂
艾美懷絲的醉鄉靈魂樂
Amy Winehouse: Back to Wine
*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既然戒不掉你,就一起醉落吧》(講師:陳昌偉,02/11/2023)
很喜歡這場讀書會的文本與電影,小說《親愛的夏吉.班恩》,與紀錄片《Amy》。看似並無關聯的兩個故事,卻可以從音樂與文字的對照中,看見小夏吉的母親愛格妮絲與Amy,兩個殘破卻又唯美的靈魂,如何一邊掙扎著振作,一邊卻又耽溺於酒精和藥物,在無盡的循環中終至殞落。
“Every bad situation is a blues song waiting to happen.”
歌手Amy出生於北倫敦,由於母親家族中有許多爵士樂手,或許音樂一開始就流淌在她的血液中。父母給予她的除了Ella Fitzgerald、Frank Sinatra的音樂,遺憾的是還有疏離而至崩解的家庭。自幼外遇缺席的父親、被Amy形容為不夠強勢而軟弱的母親,面對這樣不穩定的成長背景,Amy在父母離異後除了憂鬱、暴食,還有極度的叛逆,她化上濃厚的妝容、紋身打洞、穿著大膽而裸露,這樣的風格也一直持續她整個演唱生涯。或許自始自終,她都希望藉由這樣的叛逆喚起父親的關愛,母親也能不再軟弱,叫她該停下。
可惜,沒有人,包括Amy自己,能使她停下。
“You go back to her, and I go back to us...”
「她要待在她被丟下的地方,她要接受他施捨的任何一點善意。」
佛洛伊德在《Mourning and Melancholia》一文提到的,當與客體的關係破裂,原欲無法轉移到新的客體上,而是撤回自我,於是客體的失落成為自我的失落,正如Amy在《Back to Black》裡的那句“You go back to her, and I go back to us. ”,父親的離去如同陰影般籠罩著Amy,僅能藉由對於父親退化式的認同(regressive identifications),才能永遠留住父親。然而這樣病態的認同,帶來的是她永遠無法真正哀悼失落,接受父親缺席的事實。當Amy被禁錮在父親外遇的童年創傷中,她在成年後依然選擇與當時有另一半的Blake交往,甚至在與Blake經歷數度分合終於結婚後,又在Blake入獄期間出軌而離婚。這樣固著而病態的強迫性重複(Repetition Compulsion),就如《What Is It About Men》裡的那句“History repeats itself, it fails to die.”,創傷不斷循環,無法終結。
“Emulate all the shit my mother hated, I can‘t help but demonstrate my Freudian fate.’’
「愛格妮絲清醒時會為父親哭泣,然後為自己哭泣,她嫉妒著,夏格從未像伍立愛麗茲那樣愛著他。」
在克萊恩的理論中,伊底帕斯情節與憂鬱位置是環環相扣的。唯有放棄追求現實中並不存在的理想世界,哀悼我們無法擁有的客體,我們才能區分理想與現實。藉由憂鬱位置的修通,我們無法佔有所渴求的雙親的事實,才能被接受。不論是電影中的Amy或是小說中的愛格妮絲,似乎都停留在了妄想分裂位置(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對於父親偏執的認同與想像中的全面佔有,以及對母親的嫉妒與否定,未解的伊底帕斯,成為了困其一生的枷鎖。於是Amy始終無法擺脫兒時缺席,卻在成年後如影隨形的父親,即使她知道那是個如吸血鬼般,帶著媒體擅自拍攝她、在她身心俱疲時向經紀公司拒絕讓她接受治療的父親;愛格妮絲選擇了嗜酒而又暴力的夏格作為伴侶,並且四十將近的她依然承受著父親伍立以皮帶抽打。或許只有這種近乎受虐的她們,才是被父親愛著的。
“You go back to her, and I go back to black...”
「喝醉是為了忘記自己,因為她不知道自己還能如何才能忘卻痛苦和寂寞。」
從Amy Winehouse的詞曲中,不難看出她以音樂作為某種自我療癒的手段。但直白到近乎赤裸的呈現方式、蠻橫的自我揭露,終究無法以創作昇華那些未解的童年創傷。於是藥物和酒精成為最好的防衛,當現實與想像不存有界線,那些最原初的生與死、情與慾交融,在樂曲中一覽無遺。正如《Back to Black》裡不斷反覆、帶點魔性的旋律,最後停在了’I go back to black’,在與生命本能的拉扯中,死亡本能終究佔了上風,生命逐漸走向了毀滅。在Amy生前的最後一次演唱會,她在舞台上步履蹣跚、拒絕演唱,象徵著生命本能的創作已然崩解,她無法唱,也不願唱了。你可以說她荒誕萎靡、脫序失控,但在我看來更多的是一種控訴,甚至求救,正如童年時的叛逆,只為換得父母的關注。她想停下了,但她的歌迷、經紀公司、甚至是她的父親,They just heard, and they didn’t listen。
“Life teaches you, really how to live it... if you could live long enough.”
——Tony Bennett
整部紀錄片裡唯一讓我感受到一絲曙光、一線希望的,是Amy Winehouse和Tony Bennett合唱的那首《Body and Soul》。Amy與自己最崇拜的前輩、錄製父親最愛的曲子,Tony很好的安撫了她的緊張與不安,就像一位慈愛的父親一般,於是Amy雀躍而嬌羞、優雅而迷人的完成了這次經典的合唱。或許當她不再喝醉時,唱出的樂曲反而美得醉人。然而正當一切看似好轉,僅四個月後就傳出Amy因酒精中毒的死訊,這首《Body and Soul》也成為她生前最後一次錄音。作為樂迷以及臨床工作者,這樣的故事看來令人惋惜甚至心疼。在《The End》裡赤裸的唱出伊底帕斯情結的Jim Morrison、將《Ball and Chain》由大調改寫為藍調的Janis Joplin,都是二七俱樂部中如Amy這樣早逝的樂手。他們的才華熱烈奔放,卻又赤裸而毀滅,如流星般的生命璀璨卻又一閃而逝。
創作像是雙面刃,它可作為一種創傷的昇華,但過於赤裸的自我揭露無疑也是危險的。我想這也是治療師所能扮演的角色,我們試圖給予個案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藉由在治療室中的自我揭露,重新梳理那些未被解決的傷痛,哀悼那些被潛抑的失落。當在治療室中重現的創傷得以藉由治療師的涵容被修復,個案才有機會重新經驗那些生命中的好與壞,由分裂逐漸走向整合。
希望每個乘載著創傷的靈魂,都能被真誠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