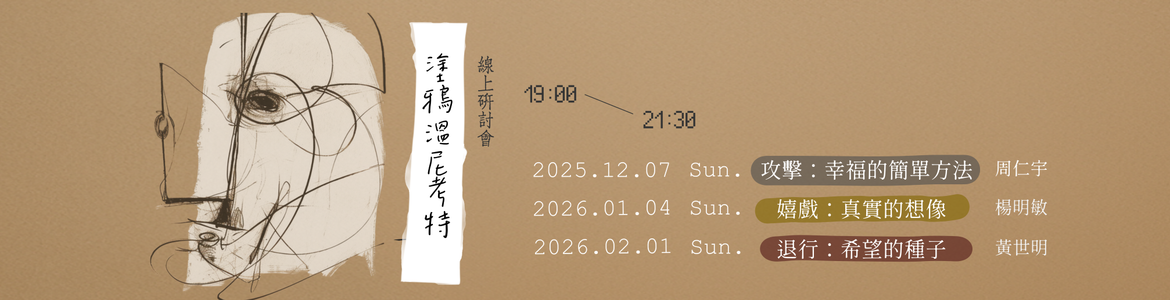To be creative or not to be creative:從《偶然與想像》到《在車上》
作者:李俊毅

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並非易事,需要強而有力的防衛、阻隔,因此形成所謂的「症狀」,這些症狀蘊藏大量不可直視、不可碰觸、不可直球對決的折衷(compromise)。這些扭曲變形的折衷狀似平靜無波,未被馴化的驅力卻競相逃脫桎梏,於是有了偶然。現實生活如此,診療室中如此,濱口龍介讓我們無所遁逃於這些偶然,每個人都得時時準備好面對,或是不面對,這些數不盡的偶然。
來到《在車上》,濱口龍介顯然換了一顆心,一個腦袋,像是他導演生涯的一個轉折,一種心境,我寧可視同精神生命(psychic life)為了活命的自然演化。這部片子改編自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一書中的三個短篇故事,以《Drive My Car》以及契訶夫劇作《凡尼亞舅舅》作為影片主軸,加上《雪哈拉莎德》與《木野》的情節穿插其中。編劇很厲害,人性的忠貞與背叛,嫉妒與羨慕,真實與虛假,天衣無縫地鑲嵌在影片的對話中。可也不要忘了影片開始《等待果陀》的一段對話,那種等待救贖的期盼與無望感,預示了影片情節的走向。
村上春樹,在《Drive My Car》一文中自始自終強調家福「靈敏地感覺到」身為演員的妻子音在拍片過程中總是與不同的年輕男演員發生婚外情,這段關係隨著片子拍完而結束。家福很痛苦地決定保持沈默,營造妻子認為他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平靜地過生活,家福甚至後來跟那些男人成為朋友也是因為妻子跟他們睡過覺的關係,家福的防衛性自虐特質果然很有畫面感。
這一點,濱口龍介在影片開始沒多久就悖離村上春樹了。家福原訂的海外演出因故臨時取消而從機場返回住處,無意間「撞見」/「目睹」妻子與外遇男演員的性愛場景,瀰漫在村上春樹讀者心中基於精神現實發展出來的想像空間瞬間凍結,觀影者的思緒自此被牢牢拴在外在現實面。學精神分析,不難聯想到這是原初場景(primal scene)的再現,而佛洛伊德所有原初幻想(primal fantasy)的基本精神是phylogenetic,也就是不強調直接目睹,而是當作somehow必然發生,村上謹守這道精神,無奈濱口龍介卻選擇將它具象化,這其實是導演的難處,卻是作家的特權。這讓我想起最近在衛武營看的一齣戲劇《碧廬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作家Henry James在書中未曾將早已身亡的不倫戀男女主角女家庭教師Jessel與男僕Quint具象化,只以無形的鬼魂隱隱約約存在,但是戲劇導演卻選擇讓兩個鬼魂具象現身,並且有口語對白。文字提供讀者寬廣無垠的想像空間,戲劇卻相對扼殺觀影者的創意,但這是現實妥協。

《在車上》精心雕琢的劇本固然引人入勝,演員之間的對話充滿較勁與試探,但是如此斧鑿斑斑的人為操弄卻相對扼殺了創意與想像,特別是跟《偶然與想像》相較之下。《凡尼亞舅舅》的選角很體貼地涵括台日韓三國演員,排練/演出時使用各自的母語之外,很神奇的加上(非口語的)手語溝通,看似創意十足,超越語言的多樣化溝通方式,但如此複雜的選角讓人懷疑濱口龍介是否屈就於某種外在現實?此外,不同於村上春樹書中的模糊與曖昧,濱口龍介一開始就把妻子音生前的外遇對象高槻檯面化、具象化。家福既隱晦也很針對性地試探、挑戰、甚至是報復高槻,而高槻也似知未知、小心翼翼地回應家福,兩人之間的競爭高下立判,最終以高槻因衝動過失殺人被捕而落幕。假如這是一場比賽,家福最後獲勝,內心潛抑的謀殺願望終於得到解放,原來矚意高槻扮演的凡尼亞舅舅這個角色終究回到家福身上,但這也是預料中,因為家福根本不想放棄這個角色。
妻子音的外遇始於女兒早夭之後,這算是一種哀悼過程;家福在車上播放他與妻子的對話錄音帶,這是家福對於逝去的妻子的哀悼,甚至進入某種程度的憂鬱;司機美沙紀的年齡正好是兩人失去的女兒(若在世)的年紀,這也算是一種哀悼與重生過程。這些都算是一場創傷的修復之旅。
妻子音因為腦溢血意外離世,使得家福晚歸矇上一層罪惡感,同時也可視為家福潛抑多年的謀殺願望(murder wish)的行動化,猶如美沙紀對於困在倒塌房子的母親見死不救的行徑,彼此如此高度認同也讓兩人敞開心胸,壓抑多年的情緒整個爆開。片末是個不免俗的happy ending,我一直覺得這畫面是個累贅,是個不必要的存在,無情地終結了觀影者的想像與創意。
 這算是一部公路電影,如同《偶然與想像》的第一段《魔法(也比不上的虛幻)》,更如同我個人鍾愛的《巴黎・德州》(Paris, Texas, 1984)。在車上,兩人形同被禁錮在密閉空間,那是個談心的絕佳時機與場合,如同診療室中的dyad,親密的心靈之旅就此開展。
這算是一部公路電影,如同《偶然與想像》的第一段《魔法(也比不上的虛幻)》,更如同我個人鍾愛的《巴黎・德州》(Paris, Texas, 1984)。在車上,兩人形同被禁錮在密閉空間,那是個談心的絕佳時機與場合,如同診療室中的dyad,親密的心靈之旅就此開展。關於作者

李俊毅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李俊毅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