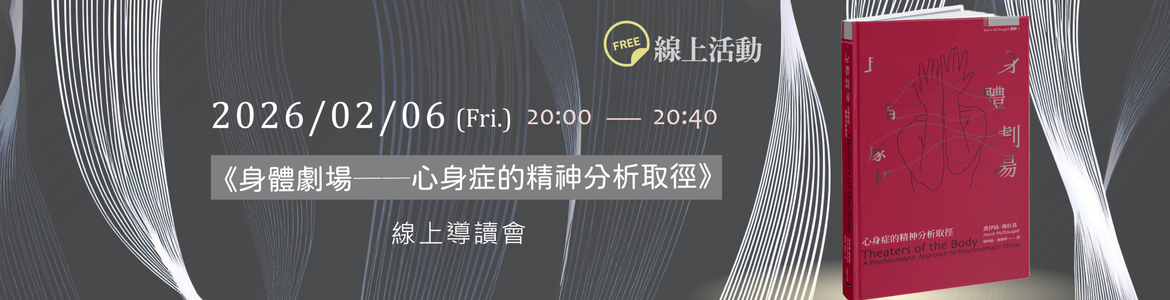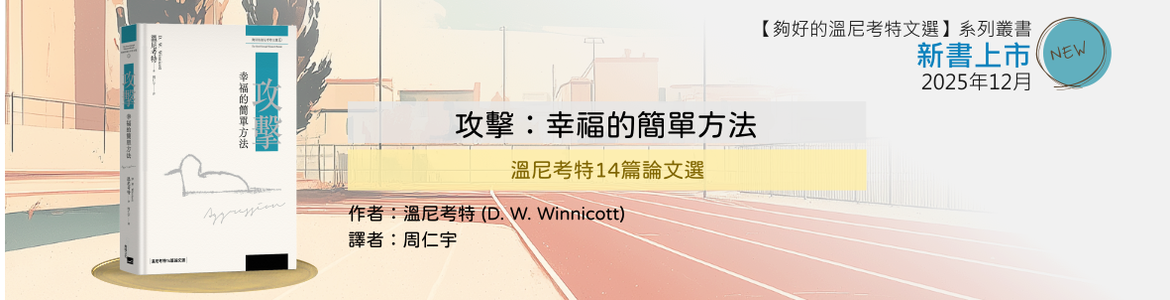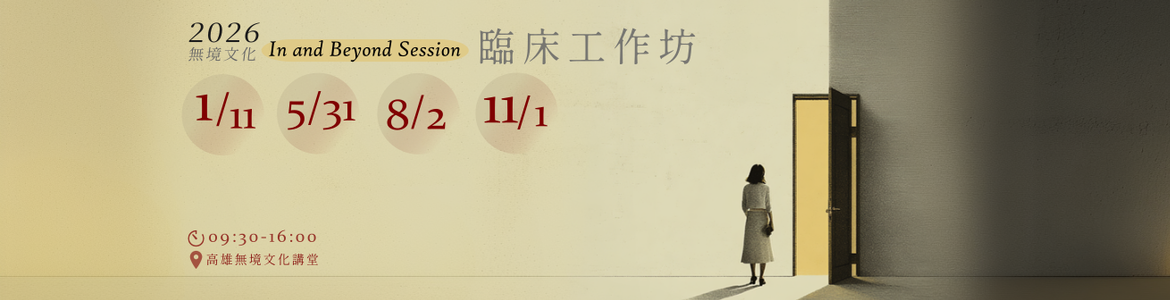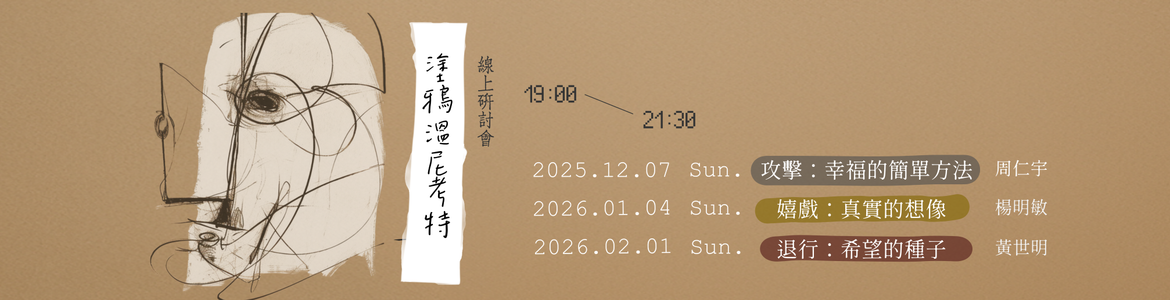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Freud and his Dissidents)
Part Ⅱ
作者:李俊毅
榮格vs. 佛洛伊德及其追隨者
阿德勒(Adler)和史泰格(Stekel)的離開,對佛洛伊德而言其實是個解脫。阿德勒所提供的內容過於膚淺平庸,完全無視於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發現,實在談不上是一門競爭學派(rival school),分道揚鑣只是時間問題。榮格的精神分析知識與學養乃至於文化背景都遠比阿德勒豐富,至少他向世界提供了某些見解,因此,榮格的離開,無論是與佛洛伊德的私人情誼或是對於精神分析發展的影響,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1906年到1910年間,榮格全心全意、熱衷於佛洛伊德工作與理論的擁護者。即使如此,在那些年頭裡,少數心思敏銳的人多少察覺到未來分裂的跡象,佛洛伊德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視而不見。榮格在1908年4月的薩爾斯堡大會中關於早發性痴呆(現稱為思覺失調症)提出「精神毒素」(psychical toxin)傷害大腦的假設,完全無視於佛洛伊德給他的建議。榮格曾經寫信給瓊斯(Jones)說他發現佛洛伊德式機轉在正常和異常兩者之間是共通的,因此「疾病」的本質只存在某種輕微的器質性腦部疾患中,這個觀點瓊斯無法苟同。
當時維也納人對榮格的質疑主觀多於客觀。在榮格手下工作了數年的亞伯拉罕(Karl Abrahm)對蘇黎世學派的玄學、占星術和神秘主義傾向感到不安,但他對於榮格的批評對佛洛伊德毫無影響,因為當時佛洛伊德對榮格抱有極高的期望。在那些年頭,即使榮格與瓊斯之間的關係友好,彼此的筆書信往返也暢通無阻,維也納和蘇黎世彼此依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敵意。榮格對於瓊斯當年不成熟的想法,亦即在1907年在倫敦成立一個類似於蘇黎世的佛洛伊德學會並未排斥,此外,瓊斯當時也已經說服日內瓦的弗洛諾伊(Flournoy)和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創辦一份以三種語言出版的國際精神分析期刊。
有一件事讓瓊斯感到震驚 — 榮格說他發現與病人討論不悅的話題時,談論細節、推根究底是不必要的,因為他擔心往後在社交場合相遇會很困窘。這其實也反映出那個年代分析師與個案之間的界限不若現在這麼嚴謹,佛洛伊德如此,榮格未嘗不是,甚至更不當一回事。榮格認為只需透過暗示,個案自然會理解整件事,不必過於直言不諱,瓊斯對此印象深刻,因為這與當時佛洛伊德處理嚴肅問題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截然不同,而這不注重細節的原則後來成為榮格教學特色之一。
菲斯特(Oskar Pfister),是經由榮格介紹認識佛洛伊德的蘇黎世學者,本職是牧師,背景理當與佛洛伊德不在同一軸線上,但他卻熱衷於佛洛伊德的理論,並且熟讀佛洛伊德所有著作,也將精神分析應用於歷史、宗教、教育學、政治、藝術和傳記領域,三人之間的通信(Freud-Jung-Pfister Triad)傳為美談。然而,佛洛伊德對於菲斯特分析辛岑多夫伯爵(Graf von Zinzendorf)的論文(1910)大有意見:「你的分析受制於道德的先天弱點。這是一個道德過於高尚、認定自己必須謹言慎行的分析師的著作。問題來了,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需要完整的闡述才能使它們易於理解,一個真正的分析過程是你從片面的表層不厭其煩地往下探索任何細節。保守的謹言慎行並不是一個精神分析的良好典範。人們必須變成壞傢伙,僭越規則,自我犧牲,背叛,表現像一個用妻子的家用錢買顏料的藝術家,或者焚燒傢俱來替他的模特兒暖房。沒有某些這類的惡行,就不會有真正的成就。」
在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分裂期間,菲斯特的忠誠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佛洛伊德向他最親近的弟子瓊斯與費倫契(Sándor Ferenczi)表達了他對菲斯特會靠向榮格的擔憂,但當蘇黎世學派於1913年7月10日正式退出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後,菲斯特只用了五天就寫信給佛洛伊德,表示他準備加入維也納協會。菲斯特隨後成為瑞士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倡導者,在1919年3月與艾米爾(Drs. Emil)和米拉.奧伯霍爾澤(Mira Oberholzer)一起成立瑞士精神分析學會(Schweizeri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analyse)。令人驚訝的是菲斯特與佛洛伊德長達三十年通信,到他在佛洛伊德的〈一個幻想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 SE21)一文中扮演匿名對話者的角色,菲斯特一生全心全意服膺於佛洛伊德和精神分析運動。
榮格對於強調性元素的疑慮與日俱增,他認為最好不要把性特質擺在前頭,特別是有關倫理議題,否則會砍斷支撐文明的樹枝,並且削弱了昇華的動力。他認為面對學生和個案時,不凸顯出性特質讓他更能取得進展。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歧異自此逐漸檯面化,未來幾個部分我們會將重點擺在兩者日漸分歧的始末。
關於作者

李俊毅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李俊毅
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