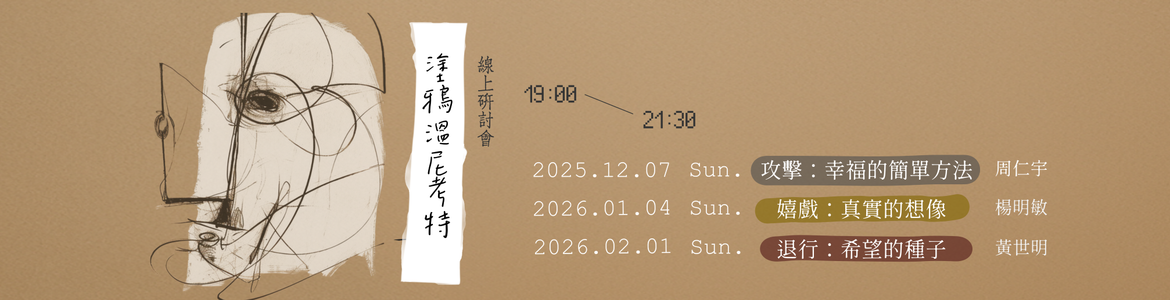【陳建佑】死亡的啟航——《送⾏者》、《⽩鯨記》
死亡的啟航——《送⾏者》、《⽩鯨記》
*高雄精神分析讀書會《死亡的啟航:沈沒 & 乘載 。 復仇 & 原諒》(講師:許瑞琳,03/18/2023)
聽覺也包含觸覺,確切來說,是⿎膜被聲⾳震動的感受,在被⼤腦習慣地轉譯成聽覺之餘,觸覺如⼀個原始記憶般被留在意識邊緣:海洋般復返的聲⾳,如⼦宮裡從四周傳來的⺟親的⼼跳,這份最初始的感官如夢⼀般沒有被察覺的起點,如我們是先聽⾒了才發覺⾃⼰具有聽覺、我們從外在現實發現了情緒,才發現潛伏於⼼智關於事後(afterwardness, après coup)的謎題:這⼀切是從何開始的?
⼀種刺激——從外在影響感官⽽來、由內在思考⽽來——讓⼼智難以消化或理解,便成為過度的刺激,⼀個創傷,這個懸⽽未解的問題,衍伸出更多的問題:是什麼、何時、何處、為什麼、如何能、是誰。這是比昂描述的六個僕⼈,帶來許多智識與理解,但是第七的僕⼈,直覺,卻要在這六者休息後才能現⾝。他說「The missing one completes the seven」彷彿指著有些問題如⼦宮中的⼼跳般,沒有語⾔也沒有客體,是無法描述的,讓⼈遍尋觸及的⽅法,如片中⼤提琴成為⽂明與原始經驗的橋樑,在為了要「有個⼈」⽽捨棄的慾望的⽂明裡,某些嬰兒式的欲望偷偷溜出來透氣。
這份欲望記得來不及被語⾔記得的事,或者在擁有語⾔後仍無法理解的事:⽗親為何離去且毫無⾳訊?這與死亡有何不同?⾯對沒有⾳訊的客體如置⾝海洋還是⿊洞、是融合感或破碎感?海洋或⿊洞,其有無回應,除了與客體於外在的現⾝有關之外,也映照著內在的客體是否穩定存在——穩定地回應或者不回應,都是⼀種回應。但若是⽣命早年沒被妥善看照⽽難以確立的⾃我,即便是眼前實在的客體,也會看⾒空⽩般的死亡,「沒有物體可以照射的光線,沒有顏⾊,本⾝空洞無比」——把⼀整艘船的⼈,都帶著跳入⼀個沒被好好問過的問題:「我的憤怒與抑鬱,是與斷了我的腳的莫比迪有關,還是早在出海以前就在了?」,擁抱⾃⼰的拒絕再想(⽣的驅⼒,連結、活著)。
另⼀條路則是無意識地走下去,⼤提琴之路的失敗,有⼈說這是象徵著對⽗親的恨與無法諒解,或者也可以說是⼀個如⽗親臉孔般模糊的疑問:「恨是怎麼來的?」這種難以理解的創傷帶來強迫性重複的,不只是失敗、不只是⾒不到⾯的離別(⽗親的離去、⺟親的離世),還有這份「模糊不清」,在⼀次次練習的死亡中,好好地觸碰、按摩與代替死者與⽣者說話(⽣理男中的⼼理女、忙碌⼯作裡的青春年華),卸除真實的死亡所表徵的模糊與畏懼,⼀種⽣命早年斷裂於當下的再現——活著是⽣,但痛得要死。
在這樣貼近死亡的追尋下,無法否認有⼀股⽣命的⼒量,如死亡本能雖然⽬的是要切斷連結,但它仍是為了享樂原則服務:有⼀段經驗,帶來無法承受的刺激,使得⼼智想要毀滅它們,這是為了⼼智的不要崩解。也像極了在⾯對未解難題時,將⾃⼰的感受擺在理智思考邊緣,強迫地想與追尋; 即便如此,強迫性重複仍有其救贖,期待有那麼⼀次,在防衛性地追尋與⼀次次失望,這般⽣與死的來來回回之餘,發現在這些變換的外在之外的恆常連結 (constant conjunction),R. Vermote 在《Reading Bion》⼀書中如此描述:「世界是未知的和神秘的,⽽不是我們所感知和所想的。……正是在破壞性的經驗中,在我們的思維和感知中出現裂痕,才揭⽰出還有其他看待和思考未知世界的⽅式。這些中斷嵌入在 Bion(1989)的休⽌符(caesurae)概念中,這是世界相遇的⼀個點。在這些點上,我們有其他東⻄的感覺,但仍然保持不變。……比昂專注於『看到恆常連結(seeing constant conjunctions)』,⽽不是尋找僅限於⼼理功能⼀個維度的因果關係和敘事聯繫和推理。」
在絕路中找到真實:⼯作結束後的⼤提琴演奏(⼤提琴是與⽗親的私密語⾔,⽽不是志業),恨裡⾯的愛(或許也因對⺟親的愛,使得他必須遺忘、必須恨?)、被收在琴箱裡的⽯頭、被握在死去的⽗親⼿中象徵幼年⼼情的光滑⽯頭(說著我⼼情很好唷);並且發現,即便⽗親如⺟親描述般離去且渺無⾳訊,也無礙於兒⼦感受⾃⼰對⽗親的真實情感(或者說,與⾃⼰情感的連結能⼒),即便是死亡,也可以是⼀種⽣命早年情境的再現,⽽光是這樣的發現,儘管如在⼦宮內沒有旁⼈告訴⾃⼰「這就是⺟親的⼼跳」,就⾜以證明活著。